男女主角分别是黄登常平仓的其他类型小说《在王安石手下当县令黄登常平仓前文+后续》,由网络作家“用户85296331”所著,讲述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故事,本站纯净无弹窗,精彩内容欢迎阅读!小说详情介绍:继续发问,黄益的背影便消失在张承的视野里。第二章张承黄益已经走出院子里一炷香的时间,张承却还坐在原处,眼睛一直盯着黄益坐过的位置。不经意间,自己竟然已经在成都府蹉跎了十几年啊,想到自己十几年前来成都府时还未到而立之年,现在已经是一身腐朽之气。二十八岁中举人,次年就中了进士,在考取功名之路上,张承可称得上是有起有伏。虽然已时隔八年,可他仍然记得殿试放榜那天,张承坐在高头大马上,头戴进士巾,身穿蓝罗袍,在众人的簇拥下,去赴琼林宴时,可谓是人生得意,顾雄自盼。连牵马的小厮都一脸得意,与有荣焉,向过往的路人介绍这是新科进士江南张承公子。琼林宴上轻歌曼舞,新科进士们觥觥交错,张承也生平第一次远远的见了官家。虽然离得远看得模模糊糊,但官家的气度...
《在王安石手下当县令黄登常平仓前文+后续》精彩片段
继续发问,黄益的背影便消失在张承的视野里。
第二章 张承黄益已经走出院子里一炷香的时间,张承却还坐在原处,眼睛一直盯着黄益坐过的位置。
不经意间,自己竟然已经在成都府蹉跎了十几年啊,想到自己十几年前来成都府时还未到而立之年,现在已经是一身腐朽之气。
二十八岁中举人,次年就中了进士,在考取功名之路上,张承可称得上是有起有伏。
虽然已时隔八年,可他仍然记得殿试放榜那天,张承坐在高头大马上,头戴进士巾,身穿蓝罗袍,在众人的簇拥下,去赴琼林宴时,可谓是人生得意,顾雄自盼。
连牵马的小厮都一脸得意,与有荣焉,向过往的路人介绍这是新科进士江南张承公子。
琼林宴上轻歌曼舞,新科进士们觥觥交错,张承也生平第一次远远的见了官家。
虽然离得远看得模模糊糊,但官家的气度可真是“仁”啊,仁就仁在那年科举官家一口气点了二百名进士,不然凭张承的才学,鲜有机会成为两榜进士啊。
张承祖父苦读诗书30年,可惜解试屡试不中。
祖父祖母半生节俭培养父翁,不知给私塾送了多少束脩,可父翁还不如如祖父,于科举场上一无所获。
虽然父翁后来在丝绸生意上颇有建树,成为县里富户,但张承祖父仍常常叹息,以为郑家耕读传家的传统要绝于父翁。
到了张承这一代,张承幼时身体羸弱又是家中独苗,几乎不能长大成人,祖父差点以为张家要绝后,哪里还有张承张承读书的念头。
谁料张承过了八岁之后,身体竟一天比一天的壮实起来,读起书来也是越来越得心应手,而后愈来愈好学上进。
十岁那年就有了神童的美誉,十二岁已然懂得所有音韵,十八岁时写出的文章,就能让祖父和父翁啧啧称赞,齐呼郑家终于出了个读书种子。
在县里渐渐有了才名之后,祖父和父翁舍了家财,四处打点,让县里保荐张承参加州试,张承当年还极力劝阻,自认为天生我材必有用,璞玉自有夺目时,何须做此等苟且之事。
可惜州里英才太多,两次州试落第,张承也老实了,再也不劝阻家里人打点上下。
与此同时县里也传来不少闲言碎语,说什么郑家公子金玉其外,
外,还被黄家家主黄益看在眼里。
黄家是青城县大户,据说京城里也有同宗族人为官。
自黄益起,族中更是多达几十人在青城县县衙为吏。
要看张承孤家寡人在青城县里一日比一日的艰难,黄益便向张承伸出了“援手”,将张承请入家中,与他诉说青城县的道道。
张承还是年轻,不明白免费的才是最贵的道理,黄家的“援手”一伸,自己顺手一接,却是上了黄家的贼船。
但上了黄家的贼船后,张承老的快了,脸上老得快,人也老成的快,没办法,寄人篱下了。
看着自己老下去,张承心里已经习惯了,但使他最难受的是,黄家在青城县的横行霸道。
刚来青城县里,张承就见过黄家是怎么害死城外的寡妇顾妇人的。
第三章 平狱那时的张承还是青城县的主簿,过端午节前一天,自己奉了令去城外催收赋税。
有道是:“抄家的知府,灭门的知县”,张承每次出城催收赋税心中都是五味杂陈,真正需要缴纳大宗赋税的富户家向来是收不上来的,城西黄家家中良田万顷,可版籍记录只需要收五百亩下等田的赋税,其余大片上等田自己也只能装作视而不见,个中缘由只能是当时令长的三房小妾也姓黄吧。
令长签发可以追缴税款的都是些穷苦百姓,可是这些人家穷得家里连过夜粮食都没有,又能追缴多少税款呢?
逼迫太急又担心出现十几年前王小波、李顺那样的强人。
张承一介书生,肩不能挑,手不能提的,万一碰见缴不了税款抗税的,可真就上天无门,下地无路,擎等着死了。
好在张承在主簿位置上也已经做了好几年,自己也不是刚出茅庐的雏鸟,略懂一点做官的门路。
所谓官字两张口,见了上官就是左右欺瞒,他们也并不全懂。
见了下属就是不懂装懂,他们也并不全懂。
上司和下属的区别在于,下属追问可以呵斥,上司追问只能被呵斥。
为官之道,在于糊弄啊。
西想东想,张承已然到了城西今日要来的平和管里,此管有人家400余户,土地本来不少,可由于离黄家太近,这几年不少人家在春秋不接之际借了黄家的高利贷难以偿还,最后只得以田地抵付,不少人家破落了起来,黄家的土地越来越
第一章 新政青城县令的家中来来往往的人络绎不绝,本县里几户大户人家都在张县令的家中哀声叹气。
“往日的常平仓多是好事,咱们几户可没少给青城县的百姓费心费力啊,结果朝廷一纸文书就把咱们的活路给断了?
不行,令长大人,这新政可不能推行啊!”
青城县大户黄家三公子黄登尽量用缓和的语气对张县令说话,可话里的急躁是怎么也压不住的。
旁边几个大户也是一脸愁容,纷纷侧过身子与旁边人议论新政。
往日里这几家大户靠着常平仓借出借回,没少在县里百姓身上捞取油水。
来了新政倒是扰了他们。
又听说本县令长预计大力推行新政,可是把他们愁得几夜没好觉,赶忙约上县长的小舅子黄登一起来找县长,希望县长给他们一个活路。
张县令倒是一脸淡然的端坐在在主位,抄起身侧的一杯茶水,在那里细细品茶。
眼见县长如此,几个富户连忙使眼色催促黄登。
黄登看自己姐夫一言不发,心里愈发急躁,也管不上那么多,叫了声:“姐夫,这新政要是推行下去,不仅咱们的活路断了,咱们的死路也快走到头了啊。
有几个仓里的粮食我们可也说不好有多少啊。”
张县令听到此言,嘴角微微上扬,脸上更多出一丝祥和:“常平仓里的粮食向来自我上任之初就是定数,这些年来也一直是定数。
青城县里有的只是贪心不足的人,从来就没有不足的粮食。”
两句不重的话落在几个富户耳朵里却有如千钧,县长话里话外是要他们补足亏空了。
自从立下常平仓后,他们几家靠仓吃仓,家里的钱财地是越来越多,历任县令也是睁一只闭一只眼,默许各家从中牟利。
可是今年新政下来,改由官府在播种之际借给百姓春苗钱替代常平仓。
如此一来,他们就不能再借着常平仓的名头把下等粮换成上等粮,也不能靠着放贷再把百姓的土地并到自己家。
今日本想找县令商讨一下,看能否不推行青苗钱,结果县令又让补上仓里一直以来的亏空,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。
“诸位还是想办法把定数补上,免得上面追查下来,闹得大家都不好看”。
眼见县令下了逐客令,众人只好讪讪离去。
黄登刚想开口,便领
多,可自己从黄家收上来的税款倒是一分没多。
张承正想税款的事,突然听到前方有人大喊冤枉,声音凄惨。
张承不禁加快脚步向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,只见不远处一头发凌乱妇人躺在地上哭嚎,嘴里还一直喊着冤枉,旁边站着个衣着华贵的瘦小中年男人,正在那破口大骂,还围着几个虎视眈眈的几个家丁状的人。
张承走近看见那中年男人之后,脚下不由的慢了起来。
罗圈腿,干巴脸,一对老鼠眼睛下架着个酒糟鼻,这人不是别人,正是城西“大好人”黄老爷的四子黄登。
由于黄家是城中大户,那时的张承平日里就没少和他打交道,只不过是坏事多,好事几乎没有。
张承放慢脚步,稳定下心神,心里盘算着,估摸着又是黄登此子在鱼肉百姓,不是好事。
今天真不宜出门啊,出门也不宜走西边。
还没等张承绕开此处,黄登看见张承便满脸笑容的迎了上来:“张主簿,几日未见气色可是越来愈好了。”
好,见到你怎么会好,张承心里骂着黄登,嘴上却是:“承黄兄关照和县令大人厚爱,最近又虚长了几斤肥肉,气色也许好了几分。”
说完便干笑几声,脚尖向另一方向转去,准备随时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
黄登老鼠眼睛一转,心里明白。
张承没问及发生了什么,明显是不想招惹这事。
可是你张主簿送上门来,自己哪有不咬一口的道理。
黄登身形一转,堵住张承去路,拉住张承衣角说道:“张大人来的真是时候,在下家里刚刚发生一件怪事,还望郑主簿定夺。
我家父翁嗜吃羊肉,这窦妇人是我家邻居,往日里烹得一手好羊肉。
今日家中宰羊,父翁便安排我将宰好的上等羊肉送至窦妇人家,委她烹好,与了她二十柴火钱,算是照顾窦妇人生活。
没想到父翁的好心肠反到害了他老人家。”。
说着说着黄登竟掩面哭了起来。
张承忍着恶心,连忙安慰起来黄登。
谁料羊肉送至我家,父翁刚尝了几块,便呼吸急促,咳嗽不止,倒在地上,父翁至今还躺在床上。
请来医官看望父翁,医官说是异物伤了喉咙,医官取出异物发现是稻草。
而后我等检查羊肉,发现发现肉里夹杂着不少青草,肉送到父翁桌上,并未经
了一记白眼,也垂了身子晃出了县令家的大门。
“换壶新茶水来”令长背后的屏风里传出一个老人的声音。
一身整洁的玄色长袍,腰间束的腰带也是黑色,却显得老人一头整齐的白发和寿眉更加精神。
屋里的人坐了两炷香,都没发现黄登的父翁,令长的便宜岳父,黄家家主黄益一直在屏风后坐着听着。
下人轻车熟路的换了壶新茶水,换上来的茶水也是黄益喜欢的明前龙井,看来早已习惯了黄益的存在。
“王相公好大的手笔,大家都说祖宗之法不可变,从汉朝延续至今的常平仓竟然也变了。
当今官家可算不得锐意进取之辈,竟也能被他说动,了不得,确实了不得啊!”
黄益两眼如炬盯着身前的地板自顾自地说道,却不看缓步走来的张县令。
“王相公向来是这样的,认定的事就像榫头伸入卯眼里,绝不回头也绝不松口的。”
张承挥手让下人退下,坐在了黄益的右侧。
礼仪之家向来以左为尊,张承坐在右侧反成了客人。
“老泰山对青苗钱有什么看法?”
张承说完这话便端起茶碗,揭开茶碗盖慢慢的水面的浮茶,眼睛却往着黄益脸上看去,也不喝碗里的茶水。
“自西汉宣帝创建常平仓制度以来,此制已越千年。
世上没有千年的王朝,能有适用千年的制度?依我看来,这常平仓倒也确实当改了,我朝的常平仓库多在通都大邑通衡要道之上建造,偏远的百姓换个粮食要跑上百里山路,过于麻烦。
自前朝唐起,我县里的借贷生意就日渐兴隆,至今日仅是我家一年就借贷数十万钱,更不消说城中其他富户家里的借贷生意。
这青苗钱是顺时之法,可谓良法。”
黄益小口啜饮着杯中的茶水,慢悠悠的说出了自己的看法。
“那依着您的意思,这青苗法属实是惠民之法喽?”
待黄益说完话几息之后,张承才敢小声发问。
“二分之息,年中散1000万贯,年末可收1200万贯。
此200万贯利息,便抵得我朝三成的岁收,仅此看来,已是惠国之法矣。
至于是否为惠民之法,老夫纵观史书,只在书里见过惠国之法,未曾见过惠民之法。”
见张承一脸疑惑,黄益脸上浮现出一丝傲睨,继续说道:“官家是强的,京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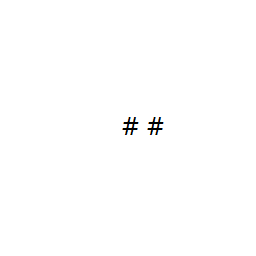
最新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