男女主角分别是泉伢子林泉的其他类型小说《一块红薯种天下全文免费》,由网络作家“一点儿意思”所著,讲述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故事,本站纯净无弹窗,精彩内容欢迎阅读!小说详情介绍:第一节:晨雾如纱,笼罩着青山脚下的桃源村。村口那棵千年老槐树静静伫立,枝丫间缠绕着昨夜未散的露珠,反射着淡淡晨光。鸡鸣声此起彼伏,划破宁静,一缕炊烟从林立的小屋中袅袅升起,像是给这寂静的清晨轻轻落下的一笔生气。林泉蹲在自家院子的石井边,正起劲儿地打水。井口被磨得锃亮,木桶在辘轳中“吱呀吱呀”作响。他一身粗布衣衫,裤脚挽得高高的,袖子撸起,露出结实的前臂。水珠顺着额头滑下,他却顾不上擦,嘴角咧着笑。他喜欢这种实在的劳作感,尤其是穿过凉意扑面的清晨,井水泼洒在脚边土地上时,泥土气息混着晨雾,似乎能洗净人心头所有的烦闷。林泉是村里数得着的年轻后生,今年不过十八,却已顶了家中的一片天。父母早亡,留下祖传的五亩薄田、一头老牛和一间破屋。他从十...
《一块红薯种天下全文免费》精彩片段
第一节:晨雾如纱,笼罩着青山脚下的桃源村。
村口那棵千年老槐树静静伫立,枝丫间缠绕着昨夜未散的露珠,反射着淡淡晨光。
鸡鸣声此起彼伏,划破宁静,一缕炊烟从林立的小屋中袅袅升起,像是给这寂静的清晨轻轻落下的一笔生气。
林泉蹲在自家院子的石井边,正起劲儿地打水。
井口被磨得锃亮,木桶在辘轳中“吱呀吱呀”作响。
他一身粗布衣衫,裤脚挽得高高的,袖子撸起,露出结实的前臂。
水珠顺着额头滑下,他却顾不上擦,嘴角咧着笑。
他喜欢这种实在的劳作感,尤其是穿过凉意扑面的清晨,井水泼洒在脚边土地上时,泥土气息混着晨雾,似乎能洗净人心头所有的烦闷。
林泉是村里数得着的年轻后生,今年不过十八,却已顶了家中的一片天。
父母早亡,留下祖传的五亩薄田、一头老牛和一间破屋。
他从十三岁起就挑起重担,五年来,不但没让家底散去,反倒种出了名堂。
村里人常打趣他:“泉伢子命苦命硬,天塌下来都砸不弯他的腰。”
他听了笑笑,不说话,只顾把手中活儿干得更好。
田是良田,靠的是他日复一日的琢磨和守候。
春耕时节,他第一个下田,最后一个收工;施肥用的是自家积了大半年的牛粪草灰混合物,比市面上的化肥还见效;灌溉更是讲究,顺着老渠一寸一寸引水,讲究一个“润”字。
他还自学了种植册子,从旧书摊淘来《农桑辑要》《齐民要术》这些古籍,一字一句抄录研读,边试边悟。
今年开春,他试着把原来三分地的水稻田改种了旱地红薯,外人笑他“脑袋发烧”,可他不急,心里有谱。
他种的是紫心红薯,一种耐旱高产、储存时间长的品种,虽然收成慢,但前景广。
他在地里铺上稻草、混合草木灰,每一行红薯苗都细心照顾,如待初生的婴儿。
邻里乡亲见他如此认真,也开始打起主意,想跟着试试。
他不藏私,谁来请教都耐心讲解。
有一次,大队长来他家视察,看到院角堆满自己做的堆肥桶和水渠模型,连连点头:“泉伢子是个人才,有这股钻劲儿,将来准成大器。”
“我不图大器,只想田好粮满,过得踏实。”
林泉笑着答,眸中却藏着不为人
经蔓延成毯,绿意浓密得几乎遮住了地面。
他蹲下身子,拨开藤叶,用木棒轻轻敲打地面,听声音判断薯块的分布。
他不急于收割,而是等每一株都吸饱了最后一口秋阳,把甜味和淀粉都蓄得饱满。
就在这天中午,村长亲自上门来了,手里还拿着一封盖着红章的信。
“泉伢子,镇里农业局来信了,说你这红薯种得好,要请你去镇上讲讲经验。
下周一,大礼堂集合。”
林泉一愣,接过信,仔细读了一遍,字字句句都朴实,却像一阵春雷在心中炸开。
他不是第一次被夸,但这是第一次被正式邀请代表村子出面。
村长看他愣着,笑着拍了拍他肩:“你小子,好好说,别紧张。
你种得好,全村都看得见,这回是该你露脸了。”
林泉点头,心里却泛起阵阵波澜。
不是因为怕说不好,而是这条“道”,终于有机会走出桃源村,被更多人看见了。
接下来的几天,他没急着准备发言稿,而是照旧每天下田、翻土、查藤、除虫。
他相信,经验不是背出来的,而是种在泥里、长在叶上的。
脚下的土才是最有说服力的语言。
他挑了几株长势最好的红薯苗,分别标记好,拍了照片,又取样做了干燥处理,用老式天平称出含水比重。
这一切,他都认真记录在本子上,每一页字迹都像他走过的土地,一丝不苟。
村里人知道他要去讲课,纷纷跑来打听:“泉伢子,你要是把那渗水坛子的法子教出去,别人学会了,会不会抢你生意啊?”
林泉只是笑:“咱种地,不靠秘方,靠良心。
教会一个,是多一个人能吃饱。
我不怕人学,只怕没人种。”
“说得好!”
村长在旁鼓掌,“泉伢子这心气,咱村百年少有。”
讲课那天,镇礼堂挤满了人,不光有各村的种植户,还有几位城里来的农业专家。
林泉穿着干净整洁的粗布衣,肩上还带着田里磨出的淡白印痕。
他没稿子,只带着一本泛黄的记录本,一脸阳光地站在讲台上。
“我叫林泉,是桃源村的农人。”
他声音不大,却字字清晰。
“我今天不讲大道理,只讲我怎么种红薯。
我用的是老方法改出来的土法子,比如埋渗水坛子,比如混合草木灰,比如稻草保湿……这些不是天上掉下来
的播种、有的在写牌子,桃源村的“田学堂”正式开课,无声却真。
午后,林泉回到自家屋里,翻出那本最旧的笔记本,扉页上写着四个字:道在人心。
他又写下今天的日期,在下方添了几句:“自由试验田开设第一日。
人心可试,土地亦可试。
世上从无完全复制之‘道’,唯有千人千地,各自成章。”
写完,他靠着门框闭目小憩。
窗外传来青蛙的叫声,远处有牛铃的脆响,一切恰如其分。
林泉知道,这只是又一阶段的开始。
他们不只是要把桃源种得好,更要把一种不靠怨天、不靠补贴、不靠押宝、只靠勤心细作的农业方式,传下去。
不是当模范,而是做种子。
夜晚来临前,林泉又去地头走了一圈,看见每一块试验田前,都插上了一块小木牌,牌上字迹各异,却都写着同一个词——“尝试”。
他笑了笑,轻声呢喃:“好。”
第十一节:夏至一过,桃源村的天亮得早,热得快。
早晨四点半,林泉便已站在合作社的晒谷场边,看着昨日收上来的第一批早红薯铺开在竹席上。
阳光透过山缝洒下,照得每一块红薯皮泛着油光,仿佛刚刚出锅的糖渍果子。
他蹲下身,一一翻看,看色泽、看干湿、看软硬。
有几块略显湿润,他立刻叫来小王:“这几块没晒透,移到东边那块强光处,下午翻一次,晚上前收回来。
别让夜露打湿了。”
小王应了声,飞奔而去。
林泉起身,望着这片晒场出神。
他记得刚开始晒红薯干那年,只有两块竹席,三口锅,全部堆在他家院角,晒场小得连翻身都难;而现在,合作社有了专用的晒谷区,还加建了遮雨棚和防虫网,每一步都是从“够用”走到“讲究”。
他走回社里办公间,一份新的文件正放在桌上。
是市农业局送来的,通知桃源村被列入“区域土地产权改革试点村”。
这意味着,村民的土地可以通过统一托管、集中种植、利益共享的方式,实现“统种统管统收”,同时也引入了风险防范和收益补偿机制。
林泉盯着通知看了许久,没有立刻签字。
他把文件压在笔记本下,走出门去。
他要先去村里转一圈,听听大家的心声。
第一家,他去了老刘头家。
老刘头正坐在门前,剥
好、谁做得勤、谁有心、谁走神。
有人提建议,有人提问题,还有人发牢骚。
他从不打断,只是记下,逐条回应。
偶尔也提问:“你觉得咱现在这套做法,像不像咱祖辈的‘共耕共食’?”
有一次,老刘头抬头说:“不像,更细了,也更讲理了。”
“那就好。”
林泉点点头,“道不是新的,是我们走回来,走通了。”
夏雨落下那晚,林泉独自走进合作社后的苗圃,那是他自己种的,一块没参与分红、不对外展示的小田。
他蹲下身,轻轻扒开一层泥,一枚新薯躺在下面,皮红光亮。
他笑了,喃喃道:“还有得种。”
半点架子。
那片试验田,是他特意腾出的,地势不同、土质不同、水源不同。
他要试,就试出真正能推广的法子。
他不怕失败,只怕把错的当成对的,误了别人的收成。
有一天,小李跑来报告:“泉哥,那块阴地薯藤长得短,可块头比阳地的大!”
林泉眼睛一亮,立刻放下手中锄头,带人奔去实地查看。
他蹲在藤下,扒开土,用手指仔细刨出一枚红薯,又闻又摸,低声道:“水保得住了,光不强烈反而糖化好,这地……有戏。”
那天晚上,他趴在桌前写到深夜,把这一项现象记录得密密麻麻,旁边还画了一张示意图。
他知道,真正的“道”,就藏在这一个个不起眼的变化里,藏在风的方向、土的温度、水的分寸之间。
一连几个月,他几乎没出过村。
但外头的事没停。
县里农业局派人来视察,市里的电视台来拍纪录片,还有企业跑来谈合作,要投资他的红薯品牌,甚至提议给他做包装、建厂房、注册商标。
林泉听得一头雾水,直摆手:“我不懂这个,我就想好好种地。”
县农业站的主任拍了他肩:“你不懂没关系,咱们来帮你弄。
你负责种,你的道咱替你走出去。”
林泉有些动摇。
他明白,一个人再强,也只能种几亩地;但如果能搭起一座桥,让更多人把地种得像他一样好,那才是走通了“道”的第一步。
于是,他点头答应试试,但提出一个条件:“必须用咱村的地,咱村的人,咱村的工艺,一分都不能外包。
我要让这红薯从头到尾,都带着桃源的土味儿。”
对方笑着答应,甚至说这正是他们最看重的。
不久,桃源村头建起了第一间合作社,墙上挂着牌子:“桃源红薯产业合作社”。
林泉被推为社长,他不大习惯开会、讲话,但凡事亲力亲为。
他招工时,优先录用本村和周边村的困难户,有劳动力没地种的、有地不会种的、有手艺却无处施展的。
“咱们不是要挣大钱,是要挣长钱。”
他常说这句话。
为了保住品质,他坚持每批红薯都做称重、编号、分级。
有人嫌麻烦,他就亲自干;有人偷懒,他便让人下田重学。
他说:“这薯不是薯,是咱村的脸面。”
有一次,城里人来下订单,提出要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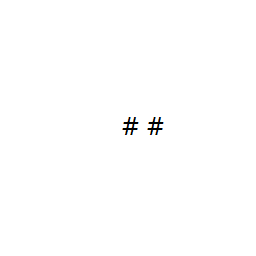
最新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