男女主角分别是抖音热门的其他类型小说《人间一瞬,岁岁平安抖音热门结局+番外》,由网络作家“大头鸽子”所著,讲述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故事,本站纯净无弹窗,精彩内容欢迎阅读!小说详情介绍:气蒸腾,阳光一寸寸洒在林间。陈平的伤好了些,虽然还微跛着,但撑着竹杖也能行走。他身背行囊,我怀抱阿念,顺着山间旧猎道,一步一步往南走。我们避开官道,沿着不知名的水脉与密林行进。日里行路,夜宿山洞或废庙,阿念乖得出奇,仿佛她也知道,大人此刻背负着不能说的沉重。陈平说,南边有个旧识,隐居在一片湖山之间,那儿常年烟水缭绕,鱼米丰足,朝廷的手再长也伸不到那里去。我问他:“你信得过那人?”他说:“他救过我一命。若不是他,我早死在宫里了。”——七月初七,天热如蒸。我们终于穿过山口,看见传说中的“清泉镇”。小镇不大,临水而建,屋舍沿岸分布,皆是青瓦白墙,水车吱呀,柳叶拂檐,一派恬静模样。阿念一见河里有人撑船打水,便拍着手笑:“船!”小平子笑了,回...
《人间一瞬,岁岁平安抖音热门结局+番外》精彩片段
气蒸腾,阳光一寸寸洒在林间。
陈平的伤好了些,虽然还微跛着,但撑着竹杖也能行走。
他身背行囊,我怀抱阿念,顺着山间旧猎道,一步一步往南走。
我们避开官道,沿着不知名的水脉与密林行进。
日里行路,夜宿山洞或废庙,阿念乖得出奇,仿佛她也知道,大人此刻背负着不能说的沉重。
陈平说,南边有个旧识,隐居在一片湖山之间,那儿常年烟水缭绕,鱼米丰足,朝廷的手再长也伸不到那里去。
我问他:“你信得过那人?”
他说:“他救过我一命。
若不是他,我早死在宫里了。”
——七月初七,天热如蒸。
我们终于穿过山口,看见传说中的“清泉镇”。
小镇不大,临水而建,屋舍沿岸分布,皆是青瓦白墙,水车吱呀,柳叶拂檐,一派恬静模样。
阿念一见河里有人撑船打水,便拍着手笑:“船!”
小平子笑了,回头看我:“我们可以留在这儿么?”
我看了看他,又看了看那缓缓流淌的溪水,忽然觉得眼眶发烫。
“可以。”
我们在镇外靠山的一处旧院落安下身来。
那是他旧识早年留下的小屋,三间草舍,两亩荒田,杂草丛生,灶台破旧。
可傍晚,夕阳从树缝中照进来时,我却觉得从未见过这般美的光。
我帮他除草,他替我补屋,阿念坐在门槛上咿呀乱唱,偶尔踩进泥里跌个屁股墩,又自己笑出声来。
我们重新种菜,种花,种豆,在屋后种了一棵杏树,小平子说:“若以后有人问起,我们就说她姓杏,名念,一念之恩,终生不忘。”
我听着,一边剪枝,一边回头望他。
他的鬓角沾了尘土,眉间却有光,像山中初阳,暖得叫人心安。
——陈平做的饭香,阿念清晨的笑,杏树开花、结果,草药枯荣,春去秋来。
这一切,虽短暂,却比宫廷十年更真实,更有温度。
冬来得比往年早些,山间的风刚过九月就已透着寒意。
我们开始准备过冬的柴火,把秋收的豆子、番薯、白菜晒干,码在屋后,用篱笆围起,防着野狗。
那晚,炕上烧着火,我裁衣,他编竹篓,阿念裹着厚棉袄在屋角摆弄干花,屋里暖洋洋的,世间一切风霜都与我们无关。
“你这衣针用得不如你切菜稳。”
他笑着揶揄我。
我白了他一
,传说曾用于战乱时皇室出逃。
小平子查了三月,买通两名老宫人,又趁冬日雪厚无人巡逻,才探得出口通向北山城外。
我脱下锦衣罗裙,换上粗布麻裙,绑起长发藏入斗笠下。
指尖冰冷,我却没有发抖。
“准备好了吗?”
他问。
我点头,轻声道:“走吧。”
——出了宫门,风仿佛带着刀子往脸上刮。
我们翻山越岭,一夜未歇。
鞋底早被雪水浸湿,脚趾早已冻得失了知觉。
我问他:“你怕吗?”
他仍是那句:“我会护着你。”
我忽然哽住,想笑,却笑不出来。
——两日后,我们终于脱离京城界线,躲进了一个荒废的山神庙中。
那庙早已年久失修,砖瓦间隙透风,庙门也半掩着,一推就响。
但好歹是个遮风之处,我们在神像背后升了小火,烤干衣物,和衣而眠。
我第一次与他并肩躺下,竟没有一丝羞涩。
他躺得直直的,一动不动。
我蜷缩在他身边,看着火堆,忽然问:“你有没有名字?”
他顿了顿,道:“宫里只唤我小平子。”
“那是宫里的名字。”
我盯着火光,“我想知道,你从前叫什么。”
他沉默了许久,低声道:“我姓陈,叫陈平。”
陈平。
多好的名字。
那一刻我忽然想,若有一日能与他做一对寻常夫妻,种田为生、煮茶读书,唤他“平哥”一声,便觉天高海阔。
<——我们的逃亡,并不是传奇,而是挣扎。
逃宫第三日,我们几乎断粮。
雪地无猎物,小村避人,我们只得靠他在林中挖出的两根野山芋充饥。
我咬一口,苦得发涩,却仍慢慢咽下。
他递来自己的半块:“你多吃些,我用惯了粗食。”
我摇头:“你先前喂我药饼时,我就看出来了——你嘴挑得很。”
他愣了一下,竟轻轻笑了:“被你记住了。”
那是我第一次看他笑,真真正正地笑,不是小心翼翼,不是强作镇定,是那种脱离宫规、没有顾忌的少年笑容。
我看着他,心一动,便握住了他的手。
日子在雪林中缓缓流过,时光仿佛失了声音,只剩脚步踩在积雪上的“咯吱”响。
我们没有方向,只朝着南边走。
陈平说那边是水乡,多村落,也多隐处。
我没问他从何打听来的,心里却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安心感——哪
殿,永远规规矩矩地站在角落。
但我知道他总用眼角的余光扫我。
我也装作未察,偶尔会故意多说几句,看他是否回应。
他说得少,但每句话都很稳重。
说风,说雪,说御花园里的桃花今年开得晚了几日。
直到有一夜,雷雨大作,宫灯尽熄。
我独自坐在寝殿中,看着窗外电光交错,心跳得厉害。
宫女都去取灯油了,殿中空无一人。
我披了外衫刚想下床,他忽然推门进来,喘着气站在门口,手里捧着一盏灯。
“小主受惊了,奴才来送灯。”
我竟有些想哭。
那盏灯暖极了,像是从他心里一路提着走来的。
我看着他问:“你……你在宫里多久了?”
他没想到我会问这个,迟疑了一下才答:“七年。”
“那你,还记得外面的世界吗?”
他眼神微动。
“记得。”
“会想离开吗?”
他望着我,没有答话。
但那一瞬间,我看见他眼中有一抹清澈的光,在电闪雷鸣的背景下,如一道裂缝,照进我心里。
——我原本并不叫知序。
进宫前,我姓沈,名知岁,乃户部侍郎之女,自小琴棋书画无所不学。
母亲常言:“女儿身亦要自持,不可仰人鼻息。”
可她却还是在我十五岁时,亲手替我梳妆,目送我登上进宫的轿子。
那年,户部失察银粮,父亲上折自请降职,以为可息事宁人,却不料被人借题发挥,连带整个沈家一同牵连。
父亲投井自尽,母亲缠绵病榻,皇恩浩荡,我被赐名“知序”,以罪臣之女的名义送入后宫。
所谓赐名“知序”,是愿我能“知晓时节,安分守序”。
从那一刻开始,我明白,在这深宫里,我不再是沈家的女儿,我不过是一颗可随时落子的棋子。
——坤宁宫冷清极了。
皇后年轻,膝下无子,自闭宫门多年,后妃虽得轮值伺候,但无人敢越雷池一步。
我初来时小心翼翼,既不敢与其他妃嫔争宠,也不敢讨好皇后。
日子久了,冷淡便成了日常,连我自己都逐渐忘了该有的喜怒。
我总在傍晚时坐在寝殿后廊,一壶热茶,一册未读完的《诗经》。
远处传来钟鸣与宫人的脚步声,合成一支单调的乐章,像在提醒我:你是这宫中千百人之一,终将归于沉寂。
直到他出现。
——他第一次让我心动,不是在灯
第一章我是在秋风起时被送入宫的。
那一年,我十五岁,正是南国落叶初黄的时节。
马车一路晃进皇城,轿帘一掀,眼前是高墙朱门、重檐飞角,还有那永远看不尽的红色宫灯,像一盏盏燃尽人心的火。
我被安排进坤宁殿。
那是皇后所居,妃嫔轮值伺候。
那时的我不过是新进宫的答应,什么都不懂,只能低眉顺眼,谨言慎行。
也是在那里,我第一次见到他。
他叫小平子,是皇后身边的内侍,传令、抬盒、打扫、送水——无一不精,无一不快。
他和那些整日咬文嚼字、眼高于顶的内侍不同。
他总是低着头,说话轻声,动作干净,仿佛想把自己藏进空气里。
但我偏偏总能看见他。
有一次,我在偏殿习字,手一抖,墨汁溅到了白衣上。
宫女急忙扑过来想擦,却被她碰得满桌狼藉。
小平子站在门外,默默地进来,递了一方干净的丝帕,也不说话,眼神温和,像是在安慰你,却又像什么也没发生。
“谢公公。”
我低声说。
他不答,只是轻轻颔首,便又退了出去。
那帕子干净得仿佛从未被人用手碰过,丝缕之间带着淡淡的香——不是女子的脂粉味,是檀香,是日复一日烧香遗留的味道。
从那之后,我便留意他。
他也开始留意我。
——皇后不喜欢我,她喜欢静。
我守在她身边,像根木头似的伫立半日,她都不会看我一眼。
倒是小平子每日来送膳送茶,总会悄悄在茶盏边放下一颗蜜饯糖,一日一味,像是在偷偷给我解这沉沉的寂寞。
我们第一次说话,是在御花园。
那天夜里月色极好,我得了半日闲,在湖边踱步。
他忽然从假山后走出来,手里提着盏宫灯,见了我愣住了。
我也愣住,两人都没出声,静得连湖水的波光都听得见。
“你怎么会在这儿?”
我先问了。
他低头行礼:“奴才奉命巡夜。”
“哦。”
我不再说话。
他却站在那里没走,好一会儿才轻轻说:“娘娘怕你寂寞,让奴才来看看。”
我一怔,回神时他已转身走远,只留那盏灯在夜里晃了一晃,像是一只小小的萤火虫。
我想了很久,从没想过皇后也会顾念我。
但再一想,却觉不对——这灯,怕是他自己点的。
——那之后,他对我愈发小心。
每次进
姓名与归属。
而如今,她躺在那里,像是一面镜子,映照出我走过的命运。
我抱起她,她好轻,眼角还挂着泪。
她张嘴吸我的手指,像是饿了。
我心都软了,一步步走回家。
屋里,陈平正在煮粥,看见我怀中婴孩,明显一愣。
“你从哪捡来的?”
“树下。”
我将布条递给他,“怕是亲娘不要她了。”
他接过那块布,沉默了片刻,轻声说:“我们收下她吧。”
“你……不怕麻烦?”
“我怕你不高兴。”
他说得极轻,却一句句扣进我心里,“她若跟着我们,至少能活。”
那天夜里,我与他轮流喂水喂粥,用旧衣裹她取暖,她终于睡了。
我们给她起名,叫“阿念”。
念念不忘,生生不弃。
——又是一年春夏交替时,山风吹开篱笆旁的野菊花,我抱着阿念坐在门槛上,看着他在院中劈柴、捡柴、做饭、修灶。
我忽然觉得,原来“岁月静好”四个字,不必用繁华堆砌,只要心上有人,手中有灯,眼底有光,便够了。
我已不再是宫里的答应。
他也不再是内侍小平子。
在柳家村,在这山水环绕、人烟寥落的小地界里,我们成了最普通的一家三口。
——但我知道,天下没有永远的逃亡,也没有彻底的忘记。
只是此刻的我,愿为这短短浮生半日,去赌余生天长。
哪怕将来天网恢恢,我也不悔这一念之间。
第三章温姓书生在村中暂住第三日时,忽然主动来寻小平子,说是愿以几件旧物换些干粮。
他带来的,是一方玉佩、一支折扇。
玉佩温润通透,扇骨用的是紫檀木,虽旧却显贵气。
陈平接过细看一眼,目光停在玉佩下方那处极淡的刻字上。
那字他认得。
是内务府专属的暗记。
他抬眼看了那人一眼,神情如常,只淡淡道:“这几样东西换些芋头干粮足够,明日我替你送来。”
温书生点头,一步三回头离去。
临走前还说:“你这人做事稳,心细,不似乡野人家,倒像是宫里出来的管事。”
陈平未答,只是抬手作揖。
他知道,这人不是普通过客。
不然怎会随身带着京中贵物?
更何况,这人住进村里后,日日在村头村尾打听“一对男女”的去向。
我从灶下听见他这话时,手中木勺险些落地。
陈平却握住我手腕,压低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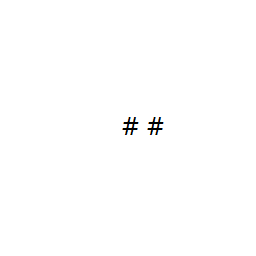
最新评论